别怀念西南联大,那样的大学永远不会再有了
摘要:拿电影来怀旧,是最好的号召方式,有好多东西,其实人人都知道,但是就像听相声,再逗乐,一个人独自笑,总给人以犯傻的感觉。走进茶馆就不一样,大家一起开怀大笑,那才叫真的乐。
微信上,网上,呼啦啦来了一堆《无问西东》的文章,我知道,有人开始怀旧了。
拿电影来怀旧,是最好的号召方式,有好多东西,其实人人都知道,但是就像听相声,再逗乐,一个人独自笑,总给人以犯傻的感觉。走进茶馆就不一样,大家一起开怀大笑,那才叫真的乐。
电影《无问西东》的片名,乍一听就是无厘头,谁明白什么意思?很多人可能会误以为,一个迷路的人在打听胡同的出口在哪里。
“立德立言,无问西东”,是清华大学校歌中的一句歌词,翻译成今天的官方语言,就是要“争创一流”,用市井语言说,就是青春无敌,不能白活。
由李芳芳执导的电影《无问西东》,是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献礼片,尽管迟到了6年,但是,有章子怡、黄晓明、王力宏、陈楚生、张震等大牌明星的加入,四个时空的新颖叙事方式,以及清华和西南联大这样的知识元素,将一大众影迷吸入影院不成问题。

我的理解是,《无问西东》是在讲述一种精神,一如多年前那本追溯北大灵魂的书,《精神的魅力》,它是想强调这样一种执着的理念:我们曾经是有精神的。
可是,精神是会遗失的,就像古迹会消失一样。
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在很多时候,怀旧本身是一种无奈,其实质是蹿动在心中的从良欲望:想回归质朴,却发现自己早已油滑不堪;想找回坚韧,却发现自己已经被现实碾压得只剩下一把软骨头。
我们的文化再辉煌,也未见得比古希腊文明更耀眼。二十年前的秋天,当我走在雅典卫城的废墟时,我敬畏地想象着这块土地上曾经诞生过的那些文化科学巨人,想象着,这里曾有过怎样的聪明和智慧。
可是,看看街头上的人群,我又在想:这个欧盟的四流国家还是当年的希腊吗?生活在这里的人还是那些让后人眩目的古希腊先哲的后人吗?我很迷惘。
清华人当然以清华园为傲,但是,他们更愿意追溯到远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虽然这是三校一体的大学,是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合并而成的战时大学,但是,清华人最愿意回顾的,还是西南联大时期,因为,那里是他们的精神家园。

如同现时的军校生向往当年的黄埔一样,清华人无疑是向往西南联大的。
这很好理解,不要说外人,即便是清华人自己,当他们漫步校园时,也只是感觉自己是在今日的清华,一所位居中国大学塔尖,与比邻的北大相互辉映的顶尖大学。仅此而已,他们不可能找到西南联大的灵魂。
精神一旦失去,便很难重新找回。就像重新站在你面前的昔日恋人,躯壳还在,但灵魂早已面目全非。
当然,清华人有理由怀念西南联大,仅以任职清华校长时间最长的梅贻琦为例,就可知道这种怀念的来由。

梅贻琦有两句名言广为人知,一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二是“我这个校长,只是帮教授搬凳子的”。其实,相比这两句话,更让人感慨的是梅贻琦家自制的“定胜糕”。
一次,西南联大一期学生毕业,为以示纪念,请校长梅贻琦来给学生上最后一堂课。上课时间为早上8点,可快到8点,梅校长却还没有出现。
学生们都知道,以往梅贻琦给学生授课,从不迟到。正在大家疑惑之时,只见梅贻琦匆匆走进教室。
他喘息了一会,说,早上我内人出去办点事,让我帮她看着糕点摊子。但是快到上课时间了,她还没有回来,我就把糕点摊子扔下,跑过来了。不过,今天的生意真的不错呢,买糕的人很多。
说完他嘿嘿地笑了,好像很开心的样子。
下面坐着的学生感慨万端:这就是堂堂的清华校长啊!当时的西南联大,由三校校长组成常委会,因南开校长张伯苓、北大校长蒋梦麟常在重庆并另有职务,学校日常校务实际上由梅贻琦主持。可是,就是这样的一校之尊,在抗战岁月也过着如此清贫的生活。
那时,联大许多教授的夫人自制定胜糕,到冠生园寄卖,一来补贴家用,二来寓意抗战必胜。在这些人当中,就有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她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卖糕时我穿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
梅家离冠生园很远,来回需要一个半小时。有一次,因为鞋袜穿得不合脚,回到家时,韩咏华的脚上都磨出了水泡。
还有一次,韩咏华参加昆明女青年会活动,有活动时各家自己准备吃食。一次轮到梅家,韩咏华却拿不出钱,就在街上摆了个小摊位,把孩子小时候穿过的衣服卖了几件,把卖得的十元钱用来待客。
同样是大学校长,我们现在的校长很在乎自己的级别,还有几个会把自己看成是“给教授搬凳子的”?我们现在的校长夫人,还有几个可以用自己的收入补贴家用,没有怨言,依然能和身居校长高位的丈夫举案齐眉,和和美美?
现在的条件固然好了,过去的事情未见得需要做,校长夫人更不必支个小摊卖孩子的旧衣服,但是,我们敢说今天的我们还有当年的那种精神吗?
西南联大的岁月是辉煌的,也是艰辛的,这在林徽因、英国学者李约瑟等人的回忆文章中看得很清楚。那个时代的学人生活在战争期间的乡野间,却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品德和气节,他们为学问而探索,为学生而努力,为国家而奋斗。

大师荟萃,人才辈出,是人们对西南联大的最好概括,他们中有学贯中西的人文大师,有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有174人为西南联大校友。
据统计,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学生中有1100余人报名参军,其中镌刻在联大纪念碑上的有834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牺牲在了抗日的战场上。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为在中国战场上协助美军抗击日军的有功中国军人授予自由勋章,其中就有曾就读于联大机械系的梅贻琦之子梅祖彦,而梅祖彦也因随军作战最终没有拿到西南联大的毕业证。
偏居西南一隅,短短数载,却留下一段辉煌的历史,西南联大凭什么能成为莘莘学子心中的一座丰碑,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巅峰?精神,学识,品德,气节,责任,或许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如今,我们走在清华园,走在燕园,依旧可以感受到清华之大,北大之博,但是,我们已经无法找到当年西南联大的那种精髓了。诚然,那里的教授依然一流,学生依然优秀,但是,作为真正的学者和学子的精神已经蜕化,在这个“不问尔西东,只羡刘强东”的商业社会里,他们和芸芸众生一样,也早已成为物质的俘虏,金钱的教民。
看着今天的学者和学子,你能想到多少精神层面的东西?不过是一群高层次的饮食男女,就像看到影片中的章子怡,我知道她扮演的是王敏佳,但是,我想到更多的是,她在浙江卫视《演员的诞生》节目中,歪着头向台上发问:袁立,你有多少年没有演戏了?
钱钟书的恩师、曾经担任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的国学大师吴宓,文革中遭受迫害,被发配回老家陕西泾阳,因患各种疾病,生活难以自理,靠在县面粉厂工作的堂妹吴须曼照料,勉强为生。高考恢复后,当他听外甥女说县城中学因缺乏师资,学生外语成绩不好时,他焦急地说,他们怎么不来找我?我能教啊!

赤子般的执着,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最让人潸然泪下的地方。如今,我们不必担心有这样的人了,因为校园内外都是一样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教师和官员、商人已没有多少区别,利益面前,人人不傻。
二十多年前,一位在台湾大学攻读法学博士的朋友到北京看我,赠送给我一本鹿桥的小说《未央歌》,他告诉我,这本写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生活的小说是台湾学生的枕边书,非常受欢迎。我欣喜地收下,却没有时间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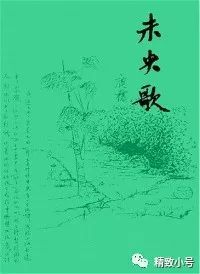
后来,我到土耳其常驻,通信中,我告诉这位朋友,那本《未央歌》在搬家时弄丢了,很可惜。不想,他在台北给我又买了一本,在我不知的情况下,直接寄到我在安卡拉的住处,令我感动万分。
工作间歇,我读了这本小说,开篇的那句话,我至今觉得清新无比:“在这大学里最大的一片青草坪中央有一个池塘。几条小河在这里聚汇。这些小河在雨季里是充满了急流的水的。因之修整校园的人对他们也不敢轻侮,由着他们任性地在校园中纵横地流着……”
这就是让几代学子心驰神往的西南联大吧?巧得很,妻子托人从北京捎来几套CD,其中有一盘台湾歌手黄舒骏的专辑《马不停蹄的忧伤》,里面就有一首叫《未央歌》,歌里有鹿桥笔下那些充满朝气的西南联大学子:余孟勤,蔺燕梅,伍宝笙,童孝贤……
这首歌的确称得上黄舒骏的代表作,曲好,词更好:“经过这几年的岁月,我几乎忘了曾有这样的甜美……为何现在同样的诗篇,已无法触动我的心弦?也许那些永恒的女子,永远不会出现在我面前……”有过大学生活的人,听到这样的歌词,有几人能不眼角潮润?
我们感叹,是因为逝去的是我们的校园时光,而对于那些观看《无问西东》的人来说,他们的感动,或许不仅仅来自于“清华”这两个字,更或许是因为,他们知道,那个让他们向往的西南联大时代的清华已经不复存在了。

曾经为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立下大功的吴宓去世于1978年的冬天,我想,在离开这个世界前,他未必会想过他曾经苦读过的哈佛大学,但是很可能会想到他曾经度过清苦日子的西南联大。作为一位国学大师,一位自尊清高的知识分子,他有一堆理由让自己的思绪,最后划过那所思想自由、学术独立、人品高洁的大学,那个在”一片青草坪中央有一个池塘“的美丽校园。
看《无问西东》,很多人内心感动,可是,这所让无数学子慨叹的大学已经定格在历史的影像之中,它将目睹它最后的孩子离开这个世界,也将目睹今天的大学校园扩得更大,楼房盖得更高。
不要怀念西南联大,那样的大学永远不会再有了。在这种逝去面前,每所学校都是平等的,清华如此,北大和南开也是如此。









